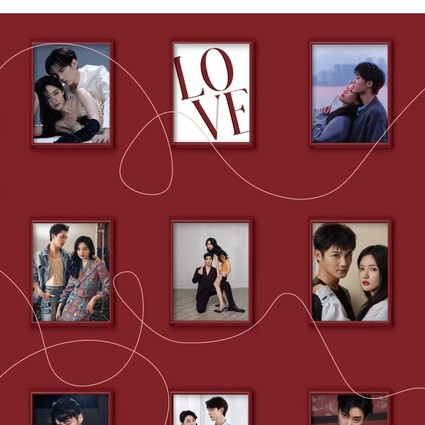《中国奇谭》,群星闪耀时
作者:时尚芭莎2023-02-12来源:时尚芭莎

他一定会走出浪浪山的,一定会的。
「孤舟行水,内心定力何来?」
自2023年伊始开播起,至最后一话更新完毕,在一个月有余的时间里,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的八部作品在B站上的总播放量已经累计超过2亿次,追番人数近550万。
前两集《小妖怪的夏天》和《鹅鹅鹅》齐齐上线后,分别因为其贴近现实的故事、绮丽诡绝的画风、殊途同归地对传统文化的深耕与表达,引发了大众的热捧,观看与讨论热度像「放火箭」一般高蹿,诸多二创随之应运而生,弹幕一度涨满屏幕,以至于工作人员不得不做过技术处理,才能保证观众打开剧集之后的正常观影。
《小妖怪的夏天》剧照
有评论说:「《中国奇谭》已经破圈成了一种『社交货币』。」
《中国奇谭》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bilibili出品、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动画导演陈廖宇任总导演,以「中国奇谭故事」这一广袤密林为母题,交由青年一代本土动画创作者在同题下自主创作。
早在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初,首任厂长特伟就提出了「探民族风格之路」的口号。后来被称道至今的诸多经典美术片,皆凝神于此。此后一个甲子多的时间里,几多浪潮,世间亦变幻数载。就在《中国奇谭》出现前良久的时间里,我们时常在种种冲击下自问:
我们是谁?我们身上的文化密码是什么?什么让我们区别于他人?多样繁复的文化长卷里,我们居于何处?若要迈步,又要往哪里去?孤舟行水,内心定力何来?
某种程度上,《中国奇谭》可以看作是年青动画人对以上这些困惑与诘问的一次纯粹而自我的作答。展卷一刻,景致分明。
《鹅鹅鹅》剧照
我们独家访问了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奇谭》总制片人李早,剧集中《小妖怪的夏天》导演於水,《鹅鹅鹅》导演胡睿,《林林》导演杨木,《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下文简称:《乡村巴士》)导演刘毛宁,《小满》导演陈莲华、周小琳,《小卖部》导演顾杨、刘旷。
他们的故事与回响,充满着具体的力量和参差的思绪,琳琅多致,和而不同,却又八方呼应。
八部动画短片一共由十位创作者分别完成。他们的年龄分布主要在「80后」到「90后」之间,高低落差大致在十岁左右。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刘毛宁——1994年9月出生。他的经历很简单,毕业后就一直在从事动画相关工作。因为动画创作风格,他被喜欢他的观众称为「动画界的贾樟柯」。
刘毛宁执导的短片《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剧照
於水、胡睿、周小琳都有海外留学、访学、工作背景。
顾杨和刘旷是一对夫妻。
除了刘毛宁之外,其他创作者都有过「动画导演」之外的工作经历与职业身份,包括但不限于:大学教师、潮牌主理人、广告策划与设计等。
李早说,《中国奇谭》是一个不倚赖任何既有IP、完全独立的原创作品,在策划伊始,大家达成的核心共识就是要在这次探索里,「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语境之间的结合」。而这些创作者自身所携带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恰恰就成为了他们在「有根的中国文化影响之下」同时能够「观察、关照现代社会」的基石。
《小卖部》剧照
於水会创作出《小妖怪的夏天》这样与现实世界高度关联的作品绝非出于偶然。他日常高频关注社会、时政新闻,喜欢的电影是《我不是药神》《站台》《大佛普拉斯》之类。
《小妖怪的夏天》剧照
胡睿小时候学了十多年的国画,「去少年宫,风里来雨里去」,那时候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一切会对自己的未来和眼光有什么影响。直到许多年后开始接触、学习电影,他才找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钥匙」。
他是听hiphop、funky,读卡夫卡、杰克·伦敦和毛姆长大的,留学时选的是德国。但在这样的文化里浸淫越久,他越「有一种冲动要发问:我在哪儿?」
胡睿执导的短片《鹅鹅鹅》剧照
胡睿对别人评价自己像伊藤润二「一点儿都不反感」,胡睿特别喜欢伊藤润二,但喜欢的是很多年前的伊藤润二。那时候《无街之城》《十字街头的美少年》——都是非常有想象里且非常深刻的天才作品,包括《墓碑镇》,看完了之后你会难以平静的。」有一天自己的名字能和他放在一起,他觉得「很沾光很荣耀」,但《鹅鹅鹅》里书生眼睛里的旋涡和人头变大的效果,「还真不是改编自伊藤润二」,那就是他「喝酒喝大了以后觉得脑子跟房子一样大的一种幻觉」。
《鹅鹅鹅》剧照
很多年前,杨木在中华世纪坛看过一个叫《古典与唯美》的展览,清晰展现了欧洲从古典主义时期进入工业革命后,艺术的流变。这让他认知到,文化的发展必须经历一个变迁的过程,要一步步、一点点演变,「不存在完全的独创」,万物都在历史和时间的根基下生长。
《林林》的一个核心母题便在于「寻找身份认同」,杨木觉得这是一件「没有办法通过理论推导出来」的事情,必须不停地尝试。他有一个师弟,专业很强,但一毕业就改行去做了金融销售,两年之后突然在即将拿到一大笔年终奖的时候离职了,回来找他,他说还想画漫画。
杨木执导的短片《林林》剧照
「人是会自我欺骗或者自我蒙蔽的,这点上相对比较悲观,我觉得你只有不停地去试、去犯错误,去丧失自我、去迷失自我,然后你才能知道真正的自我是什么样的。」
他最爱的编剧是查理·考夫曼,这位当代电影巨匠给了杨木一个「强大的理论支撑」:「必须要讲出你自己,要对自己真诚,只有这样,才能告诉其他那些孤独的人:你不是唯一的。」这让他坚信,现在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
刘毛宁的阅读体验是以《百年孤独》为分水岭的。之前他最爱读的是莫言,也喜欢陈忠实和刘震云。但马尔克斯给他带来的震撼终究无人能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他行刑之前依然能想到小时候去看冰块的下午,然后开场吉普赛人拿了吸铁石在村子里面唤起了所有物品的灵性……」
每每觉得「很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就会读几页《百年孤独》。「他让你觉得一切生命、物件、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那么的美妙神秘独特且有力量。即使他过得很悲惨,你也觉得充满了力量,你不会同情他,也不会怜悯他,但是他给你强大的力量感。」
《小满》的故事内核之一,是一个孩子如何与自己生命中最初的恐惧相遇。
陈莲华小时候第一次感到「恐惧」,是因为看到一本叫《熊家婆》的绘本,里面有一个画面,是一个小姑娘和他弟弟去姥姥家串门,有一只熊穿上姥姥的衣服,躺在床上睡觉。他讲到这里又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太恐怖了……」继续讲:「这小姑娘特别勇敢,拿了一个特长的梭,说要给熊家婆扎树上的梨,戳下来以后就往熊家婆嘴里放,借机把熊戳死了。」那本书他一直留着,但直到现在,哪怕是看到书合着的放在书柜里,「远远看见我也害怕」。
《小满》剧照
周小琳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上甲课做乙事」。她尤其对三岛由纪夫「很痴迷」,也喜欢吉本芭娜娜的小说和杨德昌、岩井俊二和高畑勋。
《小满》剧照
顾杨和刘旷已经在胡同里住了八年了。从他们住的小院出门,只消拐几个弯,一抬头就能看到护城河和故宫角楼了,再多走几步道,景山和北海白塔也能尽收眼底。自打住进了胡同,就有了更多「中国传统的东西」冲他们扑面而来。《小卖部》便脱胎于此。
故宫珍宝馆里的一尊花瓶曾经让顾杨感叹美的不俗气和海纳百川。
两个人去看过一次朋友的展览,里面提到一种古代的绯红色的牡丹,古人们会专门坐船去湖中心的亭子里,就为了看一眼这盆花,什么颜色,「特浪漫」。她喜欢丰子恺、老舍、黄永玉,觉得他们和他们的作品「生活化又俏皮」。
《小卖部》里的北京胡同
创作《中国奇谭》初期,总导演陈廖宇给两个人推荐过一位叫安房直子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家。「既美好又无厘头,又有点脑洞很大。」
小时候,家长和老师一跟他们说「要做中国的东西」,顾杨就「一股叛逆劲儿上来了压都压不住」,当长大之后有一天真的上手创作了,她才感受到了「中国的东西的那种浪漫」。
《小卖部》剧照
刘旷认知里的中国审美里的一种「空」和「含蓄」,并不只是在追求画面上的干净或简单,而是在追求一种意境:「是一种『悲』。比如你今天很伤心,就会想跟哥们儿去喝一顿,就是喝一顿,人家问你怎么了,你说没事儿,都在酒里。」
《小卖部》里很多绘画风格参考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王玉平的画作。线条几乎很少完全笔直的,比如树、房屋,许多都是不规则的造型。肌理和纹里,也大多追求「随意」和「洒脱」。「一个地方有个坑,就涂两下,但是要涂得尽量保持美感。」
《小卖部》剧照
北京的胡同本身大多比较拥挤、逼仄、曲折,地理空间有局限性,怎么在这种生存的不易中体现生活的松弛?顾杨和刘旷做了不少尝试,其中之一就是选择素人来为角色配音,他们甚至希望当中有一些口误、错误,因为这样才是真实的。
真实——这也是刘毛宁在自己的创作中不停在思索、呈现和怀疑的一件事。
他的作品中几乎总有对死亡的探讨。《乡村巴士》里的小狗、《我和吸铁石和一个死去的朋友》里的童年玩伴等等。他不回避这个命题,在于他以为:「生命,就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才叫生命,如果没有死,也就没有生。」
《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剧照
小时候他参加过一场村里的白事,是尚属青壮年的大姨去世。葬礼上,所有人都在哭,他和表哥在打闹,忽然表哥咯吱了他一下,他登时就大笑出声音来。「我感觉所有人都因为我笑那一声停止了哭泣,我立马就觉得自己做错了。自那以后每次见到我大姨家的孩子都觉得很愧疚,但他们好像已经忘了。」
今年回家过年,刘毛宁得知「王孩儿」因为疾病离世。
「疾病带走了王孩儿。」
《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剧照
杨木小的时候不爱说话,也不太合群,那时候他试图融入群体的方式「非常僵硬非常刻意」,比如「故意开一些很尴尬的玩笑,讲一些会让全场冷掉的笑话」。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不适之后,他决定彻底断绝掉心里想要融入某个团体的念头。「没有任何来往,会一点点认清自己想要什么。」
《林林》里设计了一个剧情——林林吃了人类的食物之后就变不回去了。「这是一个符号化的象征,一旦吃了人类的东西,你的兽性、本能都会丧失,你就会失去『自我』的符号……火,就是那个区分种群的存在,是一个分界线。」
《林林》剧照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场、很多场,这样的「火」、这样的「食物」。
杨木说,一个人的个性和作品的风格问题,就如同「忒修斯之船」的问题一般,大船随着时间的磨损、风雨的洗礼,不停地在壮大、修补、更替。「当它身上所有的零件都换完之后,他还是不是最初的那条船呢?」
最初——
《小妖怪的夏天》里,小猪妖一直背着的那个葫芦,只是於水为了能让造型好看点,添置在他身上的。随着创作一点点推进,才有了后来的发展:第一场他把葫芦丢在树下,跑回来拿;回家探亲,妈妈嘱咐他多喝水;结尾他被孙悟空给了一闷棍,躺在地上昏死过去,葫芦里一点点流出水……
人物、关系、铺垫、高潮、悲情、温暖,一样一样都有了。
《小妖怪的夏天》剧照
在创作《小满》的过程里,陈莲华和周小琳看了很多「地道的」古代绘画作品,其中包括《清明上河图》《五牛图》《斗茶图》《江行初雪图》《百子图》《婴戏图》等。他们特别强调——「不是二手的」、「不是改良的」。陈莲华有一个志向,想要通过动画创作,把传统文化中的绘与写,最大程度地「复原」,这需要极大的耐心与踏实,他——「耐得住。」
「当你在一幅画上看到古人的神态,和现代人完全不同,那种触动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带来非常强的动力。」陈莲华说。
《小满》剧照
「你觉得似曾相识」——这是胡睿总结的《中国奇谭》中诸多作品带给观者的感受。於水特意借用来,解释他心目中的「中国人的文脉」。「好像你去过的某个寺庙、在博物馆里看到过的某幅古代画作、小时候看过的一本小人书……很多人说《中国奇谭》让他们梦回童年,我想这就是一种对文化记忆的唤醒吧。」
哦,在这里多说一句,采访全程,於水都呈现出一种温润谦卑、吉人辞寡的气度,反复强调「世上99%的人都是小人物」;说起「有才的网友」对《小妖怪的夏天》的各种二创与深情观后感,感恩不已,并为人们内心永存的温暖而感到动容;我们雄赳赳地质问他「为什么打工人里没有女性,为什么唯一的女性角色是一个过于『传统』的母亲形象」之后,他甚至一脸慌张无辜:「我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真的想过,《西游记》里好像都是男妖怪管理男妖怪,没见过『男女混妖』……但您说的这方面我确实要多学习,对女性观众的视角以后要多多琢磨。」
只有一次,於水对于提问的回应相当斩钉截铁甚至强硬,就是当我们问及,小猪妖是否真的能走出浪浪山?
「他一定会走出浪浪山的,一定会的。」
《小妖怪的夏天》剧照
小猪妖眼下俨然成为了「打工人」不可取代的代表。
另一边厢《鹅鹅鹅》却被铺天盖地的种种猜测与解读罩了个结结实实。胡睿搓搓他因为常年把着鼠标作画而严重变形的右手小指关节,一脸委屈巴巴,又一腔风风火火:
「《鹅鹅鹅》里的书生也是打工者啊!他就是个快递小哥!外送骑手!他也是劳动者!」原作《鹅笼书生》里没写他的身份,「货郎」是胡睿在二度创作时加上的,他说自己不可能写一个王公贵族的故事,他想写的也是一个无奈的普通人。
《鹅鹅鹅》剧照
只不过他遇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现实:「你不知道事情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对面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你只能猜。」
一旦入局,人便会面临取舍,任他是什么地位身份,都会「没有那么洒脱,没有那么拿得起、放得下,都会纠结,患得患失」。
《鹅鹅鹅》剧照
胡睿在德国上学期间,有一次去威尼斯旅行,习惯了将一处风景「一马平川看到底」的他,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地方。「城市被切得很碎,都是小巷,你钻进去走到尽头一拐弯,就会看到一个广场,豁然开朗。」
由此可见,我们真的很难粗暴定义,一个文艺作品中含有的信息量到底哪些是天生携带的、哪些是后天养成的;哪些是独创的、哪些是借鉴的;哪些是东方的、哪些是西方的……
《中国奇谭》总导演陈廖宇在谈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一直以来秉承的「探民族风格之路」这一原则时说,事情的关键不在于事先定义何为「民族性」,而在于尊重每一个创作者的个性——他们活在当下,活在对每一种文化交融的理解与参透中,他们带着各自的学习和体验走到今天,不迂腐、不保守。「这些创作者是什么样的,什么就是我们当下创作中的『民族风格之路』及其独特性。」
「路」不是对人前行的限定,而是由人走出来的辽阔。
「探民族风格之路」这几个字对李早和她的伙伴而言,核又不全在「民族」,而在于「探」。
「探索,不是一定会成功或者皆大欢喜,所有人都会马上接受的,它是有实验性跟风险在里头的。」开播之前,她内心是「忐忑」的,但她又深知有些选择必须做下,并且坚决执行:包括选择和受众动画观看经验极丰富、观演交互最紧密的B站合作;带入更多商业化开发的思考和视角进入这些作品,等等。
《鹅鹅鹅》引发的争论与热议,让胡睿和李早都看到了同样一件东西:希望。
希望在哪儿?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作品被接受。因为观众已经做好这种准备。」胡睿说,即使有观众会批评他的作品「太浅薄」、「太讨巧」,这在他看来也是一件好事。「说明观众在想这件事,同时在判断和表达……观众是很多样的,也是值得期待的。」
与《中国奇谭》一起走过这一路,也让李早重新思量了「文化自信」的意涵,眼下她认为,抵达「自信」之前还需要经历两个过程,先是共鸣,接下来是认同。共鸣相对容易做到,但共鸣之后,可能是喜欢,也可能是厌恶——但即使厌恶,也会让人完成另一种反向的认同。就是需要这种不断地思考、讨论和反复,人们才能逐渐在心里达成「相信」和「自信」。
这样的「自信」中亦有传承与迭代,陈廖宇导演提及的来自上美影前辈们的「开放的思维」与「在苍白的生活中寻找乐趣的生活态度」,在一封封亲笔写就的意见反馈和回执中,被融入年轻创作者们的作品里。
作为出品方之一参与制作的上美影邀请数位老艺术家组成艺委会,对八部动画作品的质量进行把关。在两位耄耋老影人常光希和凌纾为《鹅鹅鹅》亲笔书写的分镜意见里,我们遇见了令不止一位受访导演所惊叹的「可以更极致一些」的认真指教。
「可以更极致一些」,是迭代甲子的创作精神。胡睿说自己要把老先生们亲笔书写的「激励」与「鞭策」装裱之后置于工作台前,汲取力量。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中国奇谭》并不是一个作品集,而是一个平台,可以让放飞和施展、表达和交流、认同和怀疑、相遇和相信,同时发生。
总导演陈廖宇手绘贺图
刘毛宁其实并不确定,自己到底应该和「民族风格」这件事保持怎样的关联。
「坚守和放弃都是一种伪命题。你很难说你不坚守什么,你也很难说你坚守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在放弃什么,因为你生活的养分养料已经在这儿了,我们不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你也不能回避它……创作,就是帮你去打理你的生活元素。」
他至今也没有能学会开车。这时常让他思考——「很痛苦地思考」,自己到底算不算一个合格的成年人?事实上,这也是他选择「不认同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一种抗争。
其实,这种「我到底要不要变成大人」的纠结带来的痛苦与「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带给他的折磨,是等量的。
《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剧照
《林林》结束前,杨木让所有「黑」与「白」的平衡都被打乱了,悲剧诞生。然后真正的结尾是一切归于平静。
「林林选择不再融入人类社会,接受了真实的自我;小虎违背了父亲的遗志,做了一个农民,或许无功但却可以平静地度日。」杨木说,「双方都守住了边界,于是达成了另外一种平衡……也许不是永恒的,但谁又能说得清永恒是什么。」
监制/宁李Sherry
编辑/Timmy
采访/徐妤婕 吕彦妮
撰文/吕彦妮